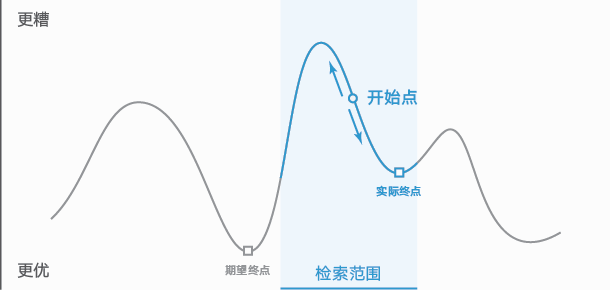展会展会,究竟还是一个行业的聚会啊。这个感觉,在礼拜六的下午和晚上,参观完 2018 年的 Armory Show 之后,变得尤其强烈。这是个艺术展,但更是个画廊行业的展。在这个展会上,「画廊」这个行业的存在感,已经远远超过了艺术、创作者本身。我十分有幸终于能在 3 月 10 日的这一天,以一种动态的、整体性的视角,对这个行业的两面,有了一个迟到的认识。
当天的早上,我是发现线上门票已经停售了,应该是当天不能预购当天的门票。原本打着网上买完票的直接进门的算盘的我,处于购票排队时间太长的担忧,赶紧急匆匆地跑出来,在 12:30 左右,经过下了地铁 20 多分钟的步行、又经过了累人的安检过程,终于拿了地图,来到了主展厅。
虽然根据门票的价格的,对整个展的估计是有一定的心理预期。但拿到地图、走进展厅的那一刻,其巨大的尺度与展览方格的密度,以及巨大的人流量,可以说都非常令我窒息。这并不是一个良好的行走空间。

事实上前半个参观的过程是相当令人难受的,无论从各个方面。整个展厅,简直要把我对于画廊这个行业最深处的厌恶统统勾了出来。明明从没这样明确地想过,但这次这感觉却格外的强烈——画框囚禁着艺术,高墙囚禁着参观的人——给了人一种强烈的不安的压迫感,仿佛是他们在用铁门无声地把我拒之门外,来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自己的易碎的身份(identity),仿佛反体制的艺术居然展现出了一种强烈的体制感(institutional)。
这种违和的气质一直存在,以至于置身其中的我长时间无法专注,简直对自己对艺术方面的爱好陷入了对本体深深的怀疑当中。我开始关注自身,关注展位的工作人员和藏家,关注着路线的结构,唯独没法关注那艺术本身。整个大半个下午,形成了强烈认同感的几乎只有一个木制的、拿着灭火器的、拼插仿佛又来自异世界的小男孩人偶,因为他那孤独的气势,仿佛映照着我内心深处的绝望呼喊。

也就从此刻开始,我注意到这样的一个展,和昨天的 Collective Design Art Fair 所传达的气质完全不一样。昨天的展,几乎可以说本身就是好客的。展品是好客的,因为可以说展览通过地面的陈设、灯光的设计,尽可能地占用方格子空间的全部面积;作品本身也是好客的,因为这些作品中的许多,都是想让人幸福地生活在其中,因此得以满足人们最浅层的需求,简直就是向我们招手;人也是好客的,原本就坐在展品中间,看我站在那里「阅读」作品,不断地问我有没有问题要问,因此交流也是温暖而愉快的。但这次的气质完全不一样。画廊那一如既往的中性冷淡的白色墙面、高悬的画作、一幅老熟人的样子在高谈阔论着的工作人员,简直在用每一分每一秒、每一个空间与角落向我诉说着这样一个残酷的现实:我不属于这里。
这样不安感的积聚,也使我注意到,在场的不安者的不只是我一个人。我看到有父母带着小姑娘参观,父母似乎是和工作人员是老熟人,但小孩子被拉着手,却在东张西望地环顾想要逃离,简直就像是曾经经历过父亲和母亲买鞋试鞋,想要逃跑因为那不是属于我的空间的小时候的我。那种整个展是一个百货商店的感觉,更强烈了。虽然展本身的确是商业性质的,用中文的话讲也可以是个交易会,但我确实没想到这种氛围,在一组又一组的人的叠加之下会是这么的强烈。我也看到了网红之类的人,在到处找地方凹造型,利用那纯色的背景拍照片;我也看着装置艺术的前面,人们摆出一副看客的样子盯着正在录像的手机。这实在难说是令人愉快的参观体验。我以为整个参观的过程,就是这样了,但我庆幸自己没有那么快放弃,终于等到了适应的时间,或者也许等到了属于我和我们的时间。
不知从某一刻起,大约是太阳落山的前后的五点左右,一切都变了。开始我还是接续下午的烦躁,但等我再注意的时候,整个世界就安静了下来了一样,我已经在以平和的心态溜达着,体会着身边的作品了。虽然这已经消耗了了我一个下午四五个小时、一个不怎么好吃意式腊肠三明治、还有一杯不怎么好喝的拿铁。
从这个时刻开始,让我引起共鸣的作家,一个又一个地浮现到我的眼前。其中第一个关注到,是由纽约的 Jane Lombard Gallery 代表的 Lee Kit。

Lee Kit 是个来自香港的创作者。他的作品,通过简单的诗句传达出绵长的思绪。有点难过、有点安静、有点寂寞,再加上色块与颜色的条带让人觉得舒服。作品中,无论是被挖开的那种感觉,还是不断划动导致凹下去的那种层次感真是很触动人,很容易引发我的共鸣。
紧接下来,一大批艺术家井喷式地浮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