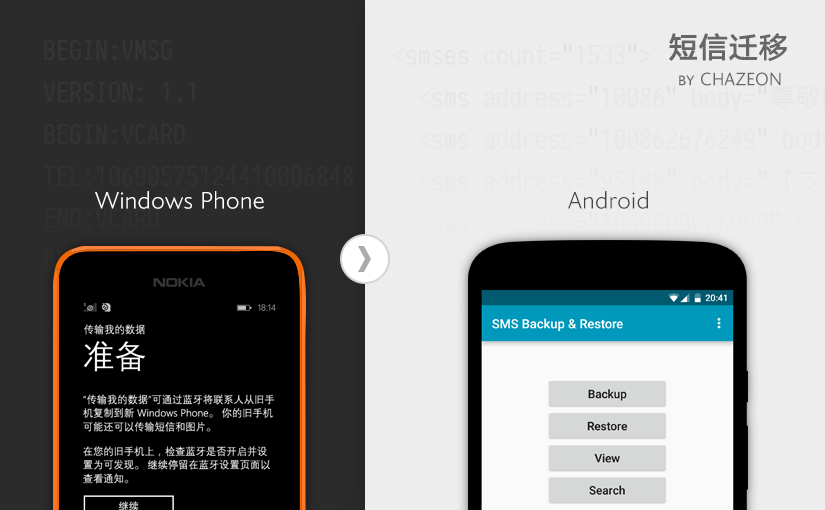德国哲学家黑格尔(G. W. F. Hegel)在《美学》第一卷开篇论序就谈到了关于人造物和自然物的地位问题
从形式看,任何一个无聊的幻想,它既然是经过了人的头脑,也就比任何一个自然的产品要高些,因为这种幻想体现出心灵活动和自由……但是像太阳这种自然物,对它本身是无足轻重的,它本身不是自由的,没有自意识的;我们只能就它和其他事物的必然关系来看待它,并不把它作为独立自为的东西来看淡,这就是,不把它作为没得东西来看待。
之前就有思考关于美的问题,甚至也考虑到美与人的影响、与人造秩序的联系,不过没有把它与「美学」这样一门已经得到了一定发展的专门的学问联系起来,更不必说认识到它与人文主义之接近程度。此前,我只能说,认识到所谓欣赏美的过程,很大程度上是从作品中体会出人的别出心裁,而没能把它与自然割裂开,更不必说把自然放在美的对立面上。这种美与人文主义的深厚根基可以说是紧密相连的。没有在人文主义的土壤中成长,使得我对于这一方面的认识很模糊很朦胧。对于人文主义的认识也是最近在阅读《人类简史》、在先锋书店与一位先生攀谈之后才对「人文主义」这一名词逐渐开始形成概念,不过现在还只停留在深层次的以人为本的很低的层次。
黑格尔在学科界定这里把这样的几组关系阐述得这样清晰,把一种飘渺的感觉落实于干净利落文字;亲身体会到这种手术式的醍醐灌顶的过程实在是震撼人心。
读得太少,想得太多,大抵若此。